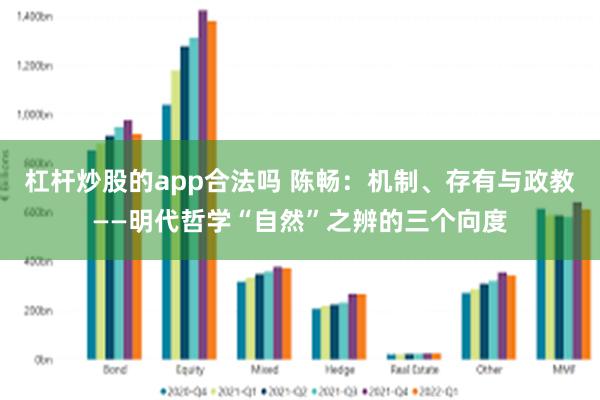

作者简介:陈畅,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哲学、现代新儒学、心性哲学。曾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系主任。获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一等奖(2019年)。著作有《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理学与三代之治:黄宗羲‘新心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出)等。
摘要:陈白沙思想以自然为宗,明代朱子学者对其有详尽的批评;而阳明学派聂豹与王畿,甚至刘宗周中年与晚年两个阶段,对陈白沙“自然”思想则有不同的认知与评价,从而分别展开复杂的思想辨析。由此,明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围绕白沙展开的理论辨析,构造出自然之辨的独特思想论域。本文通过对明代 “自然” 之辨的理论辨析,探讨 “心”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一方面,明代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 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辨在时间上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总而言之,通过明代自然之辨获得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深入理解明代心学思潮的多层次意蕴,如心学与政教秩序之间的复杂关联等,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自然 心学 政教秩序 陈白沙
引言:问题与路径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观念蕴涵非常丰富。概言之,“自然”主要指充满生机的天地宇宙“自己如此”“本来样子”之意;它指示出一个自发、完美而和谐的状态,其中排除了造物主的观念,亦杜绝任何人为制作的因素。在宋明理学中,自然的重要性表现在理学家普遍将其确立为天理良知的核心内容;如程明道所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1]而哲学家对“自然”多重内涵的不同侧重及其运用,正是吾人藉以考察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所在。从理学家的使用情况中,可以概括出天之自然、人之自然等用法;[2]前者如春夏秋冬之往复、日月星辰之运转,具有公共必然、秩序、规律的涵义;后者如人的情感和工夫修养所指向的不思不勉境界,具备个体生命与情境的涵义。更由于人的生命牵涉到语言、历史与社会政治等内容,故而个人与群体共在的公共社会之建立,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特质——在守护人之自然本性的基础上确立政教秩序[3]——在此豁显无疑。如杨儒宾先生所论,“自然”在理学家的用法中是作为状词来使用的,用以描述理学的形上学、工夫论。这主要是源自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特性,此超越的内在性见之于自然世界,也见之于人的构造。[4]正因为这种特点,作为状词的“自然”能够以一种别致的方式让吾人深入了解理学的深层意蕴。吾人对于宋明理学的本体、工夫与政教秩序的探讨,由此具有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明代哲学家陈白沙提倡“学宗自然”,[5]对后世哲学思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明代哲学家围绕白沙自然思想展开了非常详尽的批评、辨析引申和推进。批评来自朱子学阵营,从胡居仁、罗钦顺到顾宪成,明代朱子学者强烈批评白沙自然宗旨,转而提出自己的自然思想。辨析和推进来自阳明学者,阳明学者普遍认同白沙“自然”思想,同时与阳明学派内部对良知教不同发展方向的辩论同步,展开多层面的理论辨析与推进。本文将通过分析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前提预设与概念构成,厘清其中最核心的“自然”三义:一、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二、作为根源存有的自然;三、作为政教秩序基础的自然。白沙与朱子学者重视机制涵义,并且此义与《中庸》“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契合,两家辩难转而为对“不思不勉”与“思勉”关系议题的诠释。这也展现出白沙学术与朱子学在理论上具有某种同构性。王阳明和王畿重视存有涵义,在王畿的诠释中,阳明与白沙学术具有本质性差异:阳明将白沙“自然”宗旨的静养顺率,转变为良知之主动创造。阳明后学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则注重政教涵义,这种特质建立在其对朱子学、阳明学流弊的解决基础上。
通过上述思想史脉络的疏理与诠释,吾人将发现,自然之辨的理论实质可概括为个体性与公共性关系之辨,它展现了宋明理学对于本体与工夫、时代政教秩序的多层面思考。换言之,在白沙自然宗旨的基础上,明代哲学家们建立了一个自然之辨思想论域;吾人通过疏理与分析这一论域,可以获得理解明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视野。
一、白沙心学与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
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源头与主线,是陈白沙思想的评价问题。白沙的思想创新开明代心学风气之先,推动学界打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6]的僵化、沉闷状态。明代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阵营在此问题上壁垒分明:前者视之为禅学异端,后者盛赞其为圣学。由此产生明代哲学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之一:白沙“学宗自然”,而明代朱子学者却一致批评白沙不明“自然”真义、近禅;思想界由此被充分调动起来,各方围绕自然展开了蕴含丰富的思想辩论。
如前所述,理学家对自然用法可概括为天之自然、人之自然等涵义。白沙思想中的自然,首先是在天道的意义上言说。 例如,白沙称:
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 [7]
天地之间四时运行不停歇,百物蓬勃生长,均体现了天道创生的意义,这就是天道之自然。人与天地同体,亦应效法天道之自然,以契入和体现天道。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儒家的创造性本身,从人讲为仁、为性,从天地万物处讲为天道。……中国的传统精神,儒教立教的中心与重心是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 [8]上引文中白沙所说的“以自然为宗”,便是在如何体现天道的意义上言说。白沙认为作为造化之主的天道,最重要的特质是生生不息,不滞在一处。这实际上就是朱子所说的“通”:“天地之化,生生不穷,特以气机阖辟,有通有塞。故当其通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当其塞也,天地闭而贤人隐……”[9]天地之间充盈生生之机,万物本真地处于互相敞开的境域,处于一种动态、生机的关系之中。这是理学家共同认可的天道内涵。不同的是,朱子认为只谈论气机生化、动静阖辟是不够的,天道最重要的内容是动静背后的“所以动静之理”,亦即太极; [10]而白沙则认为天道的创生性体现在鸢飞鱼跃、通而不滞的生生化化过程中,由此判定朱子的太极之理“太严”。 [11]在朱子,太极、天道(天理)是天地万物的超越根据,是能够以理性加以把握的根本法则,在确认生机的同时也将其先验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天道、天理之自然,表现在天理是“天地之间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假毫发意思安排,不着毫发意见夹杂”,[12]能抑制个人私见并起到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效用。然而,人心是生生变化的活物,朱子天理观在限制生机的同时亦限制了心的活力,甚至可能导致对生机的遏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荒木见悟将朱子作为“天地之间自有一定不易之理”的天理观称为先验地限制了心的定理论,[13]甚为恰当。这就是白沙认为朱子之天理观太严的根源。上引文中,白沙提出“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则是通过松动朱子理论中对心的先验限制,恢复心的活力或者说是此心生生化化之机,以实现天道的创生性。综上可知,白沙思想中的自然是在天道创生性机制意义上使用的。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明代朱子学者对白沙自然思想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在本体论层面的理气之辨、心性之辨。 朱子学者从定理论的立场出发,批评白沙将生生化化的活力和创生性赋予心的做法。例如,白沙同门胡居仁批评白沙之学“认精魂为性”。 [14]该批评源自理学家惯用“鸢飞鱼跃”表述自然天机,而程朱一系理学家解释《中庸》“鸢飞鱼跃”时称:“会得的活泼泼地,不会得的只是弄精魂”。 [15]显然,胡居仁是批评白沙不明自然真义,徒然耗费精神。因为从朱子学的立场看,气机是形而下者,道义则是形而上者,两者不可混淆;白沙从气机生化论述的自然只是“以气为性”“认欲为理”而已。罗钦顺也从这一立场出发批评白沙之学不能极深研几。 [16]依唐君毅先生的解释,这是批评白沙之学只及于虚灵眀觉之心,未能及于绌静精微之性。 [17]从形上学的层面看,理气之辨与心性之辨涉及的问题是一致的,都是形而下者与形而上者之辨。黄宗羲对此有一个分析,他认为其根源在于罗钦顺等人错认心性为二,由此错误批评白沙明心而不见性。换言之,这涉及心性(理气)一还是二的哲学立场差异,并非白沙的失误。[18]黄宗羲观点的深入之处在于指出双方哲学立场上的差异。至于是否可以直接论定白沙主张心性合一,则需要结合下文第二维度的辨析来判断。
第二个维度是在工夫论层面的思勉与不思不勉之辨。明代朱子学者强调天道自然所具有的规律性、必然性涵义,批评白沙之学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然。晚明东林学者顾宪成由此批评白沙自然之学导致错误的“不思不勉之说盈天下”,流弊不已。他认为真正的“不思不勉”是指“行乎天理之不得不行,止乎天理之不得不止”,一般人需要通过各种后天强制性的“思勉”功夫锻炼才能掌握之,最终达到“不思不勉”的自然境界。[19]罗钦顺也从这一立场出发,批评白沙的静养端倪工夫所得“不过虚灵之光景”。因为白沙一味静坐,缺乏日常经验的锻炼,根本无法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 [20]如前所述,白沙对朱子学天理观过于严苛的特质感到不满进而提出思想创新;而朱子学者的上述批评却是基于白沙所不满的特质,可见这种批评并不相应。白沙弟子湛甘泉曾针对类似的质疑作出回应,他强调白沙主静思想的主旨,与《中庸》“先戒惧而后慎独”“先致中而后致和”,以及朱子“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等思想是一致的。[21]甘泉的辩护非常关键,事实上这是理解白沙自然思想最重要的切入点。
湛甘泉的回应说明了白沙学与朱子学具有某种同构性。 以白沙著名的“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22]思想命题为例。这一命题的关键是端倪。白沙本人的解释是:“上蔡云:要见真心。所谓端绪,真心是也。” [23]谢上蔡曾举例说,见孺子将入井时的恻隐之心就是真心,其特点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地自然生发。 [24]这里提到的端倪、端绪、真心都是对自然生机的表述。白沙指出要在静中坐养出端倪,正说明其最重要的内涵是未经人为因素污染、未被人类理智和观念歪曲。白沙文集中多处地方提及养出真心的过程与状态;例如他主张心具有“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主张“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 [25]从这些文献可知,白沙力图打破“太严”之理对于对生命的限定,主张回归于未经“太严之理”穿凿的自然本心,由此获得富有天机意趣和创造性的生命状态。这与道家“无”之智慧颇有可比较之处。牟宗三先生在论述道家“无”的哲学时指出,道家有让开一步的“不生之生”智慧,开其源让万物自己生长。[26]显然,白沙主张回归于未经穿凿的自然本心,可视为采取了从“太严之理”让开一步的思维,与道家“无”的智慧亦有类似之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白沙所说的天道自然是儒家意义上的积极创生。 [27]本小节篇首对于白沙天道自然观内涵的论述已足以说明。此处再举两例以进一步证之。在白沙的文本中,大量使用“机”“妙”“神”等词汇以描述自然生化,其目的显然是展现天道活泼泼的创生机制。此为例证一。例证二,见于白沙描述的宇宙本然秩序是“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 牛自为牛,马自为马;感于此,应于彼,发乎迩,见乎远”,[28]亦即天地万物均自然申展(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自为)而又富有生机地关联为一个整体。这种每一事物不受外力干扰而自然、自由地生长的天道机制,能令天地万物以最高效的方式组织起来发挥创造性的效用。而白沙静养本心的目标,就是通过心之静澄工夫契入这个天道机制,在日用间顺率此天道而行动。
综上,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处理的核心问题是道与物之间的生化、创生关系。心之自然是天道生生化化之活机的一个入口(端倪)。 这也表明,白沙所论心性之关系,并非以心为主导,而是以道为主导,以道融摄心性。因此,上文黄宗羲所论白沙思想中的心性合一特质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其同时亦需要进一步确认为心与性皆契入道而为一。与阳明思想比较起来,这一特质尤为彰显。如后文将要论述的,白沙以顺率天道秩序为内容的心之自然观,区别于阳明以存有论意义上的主动创造为内容的心体观。上文引用的白沙弟子湛甘泉对其师的辩护,事实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说明。因为白沙的道物观,与朱子学体立而后用有以行思想,实际上是同一套体用论思维。双方在确认心要契入天道自然这一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差异在于各自体认的契入方式并不相同而已——白沙之心体自然是天道生化之端倪,端倪即意指其本来并非为二,静养端倪则是心契入道而展现其本来为一的途径; 朱子学则将天道(天理)视为心外之物(心、理为二),以心认知天理为途径。由此可见,作为白沙思想起点的朱子学,的确在白沙思想结构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这些都表明白沙与阳明思想之间具有微妙的差异。当然,这只是在明代心学阵营内部的义理差异。因为,白沙承认心与性(理与气)、心与道的本来为一,此为明代心学的基本立场;却与朱子将自然或天理视为心外之物的哲学立场差异很大。并且,白沙自然思想赋予心以积极的活力,指出心具有虚圆不测之神用、能够洞察事物的动静有无之机的本然状态;这种思路毫无疑问是明代心学对心之创造性的一种开发途径。
二、阳明心学与作为存有的“自然”
笔者曾着文论述阳明对“自然”用法大致可区分为三种互相蕴含而又稍有区别的涵义:1.无为(自在,毫无掩饰造作的纯真);2.自发的趋势(自动,不容已);3.规律(秩序、必然如此)。 [29]在实际的语境中,这三种用法将天之自然、人之自然的涵义错综交织在一起,展现了阳明心学独特的思想结构。而对自然思想的分析,是吾人理解阳明去世之后阳明学派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这首先体现在对白沙自然思想的评价问题上,阳明第一代弟子有尖锐的对立意见。这种对立构成阳明学派自然之辨的核心议题。
阳明对白沙的态度问题存而不论。[30]在阳明去世之后,阳明第一代弟子对白沙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王畿提出“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观点,影响深远。他认为白沙“以自然为宗”之学是孔门别派,而阳明动静合一的良知学直承孔子“兢兢业业,学不厌、教不倦”之旨,为圣门嫡传。[31]聂豹则推崇白沙自然之学,“平时笃信白沙子‘静中养出端倪’与‘欛柄在手’之说”,有“周程以后,白沙得其精,阳明得其大”之论。 [32]评价差异的根源,在于双方对良知学发展方向的理解产生了严重分歧,而白沙自然思想就成为双方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或直接理论来源。
从王畿与聂豹“自然”之辨的文本来看,双方的关注点集中于白沙学与阳明学的两个对立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工夫论上的主静与动静合一之对立。王畿指出,“师门常有入悟三种教法:从知解而得者,谓之解悟,未离言诠;从静坐而得者,谓之证悟,犹有待于境;从人事练习而得者,忘言忘境,触处逢源,愈摇盪愈凝寂,始为彻悟。” [33]在他看来,白沙主静工夫只是作为权法的证悟之学,不同于阳明无分语默动静、从人情事变彻底练习的彻悟之学。如前所述,白沙静养端倪的工夫要求隔绝于外在环境,以类似于道家“无”的工夫消解形躯与世俗的羁绊,以“我”的让开一步,令天道秩序自然开显。这种工夫论不只是强调有待于静养的工夫入路,在修养境界上也呈现出对于更为广大高明的天道秩序之顺承(静)的风格。牟宗三先生批评白沙把实践工夫当作四时景致来玩弄,有流于“情识而肆”之嫌。这个批评是基于牟先生对于心体的存有论内涵阐释而来,对于厘清白沙与阳明自然思想差异极有启发意义。阳明指出,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34]按牟先生的分析,这个命题是指良知之心不是一认知心,而是具有存有论内涵的形上实体天理不是外在的抽象之理,而是由真诚恻怛之本心自然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不是抽象的光板的呈现;而是性体心体本身之呈现,亦即在经验中而为具体的真实的体证与呈现。本心觉识活动的内容不是认知外在的理,而是心自身所决定者;就此决定活动本身说,良知是即活动即存有的。[35]在这一意义上,阳明所说的“良知自然”是有积极和真实内容的觉情,是本心不容已力量的自我跃动,它为道德行为提供标准和动力;而白沙则是在消解或做减法的意义上讲静澄之心。对比而言,白沙主静工夫的确偏于神秘内省,主要在精神境界的层面着力,稍有不慎便有流于光景之弊。阳明致良知工夫则不同,良知是道德本心同时亦是形而上的宇宙心,致良知工夫的要点是令其充分呈现出来并见之于行事;“致”之工夫是积极而动态地随事推致扩充于实地,无分于动静。由此可见,王畿对白沙与阳明之间的证悟与彻悟之辨有其合理之处。有趣的是,聂豹对白沙主静工夫的诠释与评价完全不同于王畿,他强调“静以御乎动”并以此克服阳明动静合一之学的流弊。聂豹的诠释展示出白沙主静工夫尚有另一层内涵,此见于双方自然之辨关注的第二个命题。
王畿与聂豹“自然”之辨关注的第二个命题,是体用论层面的“即用见体”与“体立而用自行”之对立。王畿与聂豹围绕“良知是性体自然之觉”议题展开辩论。在辩论过程中,聂豹重点关注的是性体,王畿侧重于觉。由于双方关注点有异,自然一词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蕴涵。王畿说:“触机而发,神感神应,然后为不学不虑、自然之良也。自然之良即是爱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虚,即是无声无臭,天之所为也。”[36]显然,这是在阳明自然三义中的无为与自发的趋势意义上来诠释,而支撑这一诠释的则是王畿“即寂即感”“即未发即已发”的体用浑一论。如前所述,阳明“天理之自然明觉”一语是指天理在心体中具体而真实地呈现,它不是一个有待认知的抽象概念。这种具体而真实地呈现,就是性体自然之觉或称为自然明觉,亦即王畿强调的无为与自发。因此,王畿诠释的“性体自然之觉”之自然,是在未发已发浑一、寂感浑一、心体即性体的意义上说。
事实上,王畿的诠释是符合阳明原意的。阳明论“未发之中”为“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其表现就是未发在已发之中、已发在未发之中。[37]此即阳明即用见体的本体观:一方面,心体即性体,不存在超然于本心的超越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寂感浑一、未发已发浑一,良知之自然明觉就是良知(性体)当体自己。这一体用观确保良知的创造性在每一行事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实现,但同时也造成了另一层的效果。因为人心当下呈现的,不一定是良知,可能是肆无忌惮的情识,也可能是玄虚事物。所以在当下之“用”中自然呈现的,不仅仅是超越的道德理性,亦有可能是情、意、欲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存乎心悟”[38]是这一体用观得以发挥理想效用的前提。悟则良知呈现而自作主宰,不悟则此心从躯壳起念。由前者,如阳明《拔本塞源论》描述的“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39]的真诚恻怛之情,便能通过良知学的体用结构获得广大高明的意义;由后者,人心则被局限在情识或玄虚当中,带来种种弊端。问题在于,心悟与否是由个体自行体证,这就无法避免由于误认或过于自信而带来的鱼目混珠、自以为是状况。当阳明学作为一种教法风行天下以后,即用见体观引发的情识与玄虚之弊便难以避免。牟宗三先生认为这些弊端是人病,而非法病。[40]但是,站在儒者维系世教的角度来看,阳明学派学者势必要在理论结构上做出改进。聂豹与王畿开展的辩论,就展现了这一努力。
聂豹的改进措施便是退回到白沙自然之学体立而用自行的体用论模式。聂豹在辩论书信中答复王畿:“欛柄、端倪,白沙亦指实体之呈露者而言,必实体呈露,而后可以言自然之良,而后有不学不虑之成。” [41]此处所说的实体,就是性体。聂豹充分认识到即用见体的流弊,在于人心无所拘束容易造成情欲的自然、自由发散。因此他根据白沙体用观,将良知分拆为虚明不动之寂体(未发之中)和感发之用(已发之和)。在他看来,感生于寂,和蕴于中,真正的致良知工夫应该是“立体”工夫;而王畿所言作为明觉的良知只是在感发之用的层面,不是真正的良知自然。在聂豹看来,致良知教的前提是性体之确立,然后才能呈露于本心之中并随事自然推扩出去。聂豹的意图是在心之上树立一个超越于心的形上实体,由此重建致良知工夫得以可能的前提。在这种体用结构中,性体能够避免人心被局限在情识或玄虚当中,但是其后果是心不再具有存有论的涵义。这一特质导致聂豹的思路在救正良知学流弊的同时,亦受到了根本的质疑:未发已发(寂感)浑一是良知学的基本结构,不容许分拆为单独存在的未发与已发。因此,黄宗羲评论聂豹及其盟友罗洪先“举未发以救其弊,……然终不免头上安头而遭到同门环起难端。”[42]这种理论对立,就是中晚明时期阳明学派难以解决的困局。
综上,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心与物之间的创生性关系。阳明心学中的心体自然是在存有论意义上的表述,其思想结构是心体即性体。由此导致人之自然与天之自然涵义贯通为一,心体本具的不容已力量的自我跃动,以无为和自发的方式展现性体秩序。这与朱子学、白沙学都完全不同。如果说白沙的自然之心是顺率天道秩序的静澄之心,那么阳明的心体自然则是存有论意义上的主动创造。另一方面,虽然白沙主静工夫如牟宗三先生所批评有流于光景之弊,但聂豹的阐释表明其天道自然观蕴涵的以人心契入天道自然秩序的途径,能够救正阳明学流弊。这在晚明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心学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阐发。
三、刘宗周、黄宗羲哲学与作为政教的“自然”
从现存文献来看,刘宗周对白沙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批评到推崇的转变。刘宗周50岁时的著作《皇明道统录》现已佚失,该书对白沙的评论文字保存于黄宗羲《明儒学案》一书的《师说》部分,其中使用了朱子学者的口吻批评白沙主静自然之学为“弄精魂”之禅学。[43]而在记录于刘宗周62岁至66岁期间的语录,却表达了对白沙学说的推崇,并感叹于50岁时的误解:“静中养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独即天”“静中养出端倪,今日乃见白沙面”。 [44]笔者的前期研究已指出,刘宗周思想以57岁为界,57岁以后方为晚年成熟期思想;其晚年思想与50岁时思想具有结构性的重大差异,故而对白沙自然之学的评价亦截然不同。[45]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发生上述变化的根源在于刘宗周找到了一条不同于江右王门聂豹的思路,创造性地将白沙自然之学与阳明学结合起来,解决阳明学派的内在困境。上引两则语录代表着刘宗周从白沙那里得到启发,但并不表示他简单地回到白沙的立场,因为刘宗周晚年慎独哲学的义理结构与白沙学有较大差异。而晚年刘宗周从白沙自然之学得到的启发,主要表现在他修改了阳明心学中心体即性体的浑一关系,改为未发已发一体而有分的体用论,并由此重新诠释“端倪”。 [46]自述“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47]的刘宗周忠实继承者黄宗羲,对此亦有精彩阐述。对比,本文从三方面加以说明:1. 刘宗周、黄宗羲心学思想的外王面向;2. 刘宗周自然思想的义理结构;3. 黄宗羲对师学的独特阐释。
第一,关于刘、黄师徒心学思想的外王面向,要从刘宗周思想中浓郁的救世情怀说起,而驱动刘宗周思想从中年推进到晚年阶段的根本动力亦在此。刘宗周处于晚明大厦将倾、危机四伏的时代,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秩序都在崩溃边缘,他认为祸根在于学术不明,人心不正,而“救世第一要义”就在于解决学术流弊。 [48]明清鼎革之后,黄宗羲也指出“今日致乱之故”在于“数十年来,人心以机械变诈为事”。[49]师徒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问题是,为何刘宗周所说的学术具有救世的功能?原因在于,理学形上学是在根本上塑造着宋明时代的政教结构。且以朱子天理观为例作出说明。朱子对天理的定义是:“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50]所当然之则是指事物变化的个别性之理;所以然之故则是指超越个别性限定的根源之理、结构之理,天下万事万物因此而被纳入相互通达、彼此相与的贯通状态。笔者此前的研究指出,上述两个涵义分别代表个体性与公共性,说明天理观内在蕴含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恰当平衡结构。这是理学家针对宋代以后平民化社会“一盘散沙”之政教秩序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最根源的政教意义。[51]在这一意义上,将机械变诈之人心引导回礼义主宰的轨道,就成为刘宗周、黄宗羲学术救世的首要任务。
刘宗周所说的学术不明是有其明确指向的,此即朱子学与阳明学流弊:“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宪成之学,朱子也,善善恶恶,其弊也必为申、韩,惨刻而不情。”[52]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刘宗周之学乃乘阳明后学玄虚、放肆之流弊而起,[53]这段文字则指示出刘宗周之学的另一面向是修正朱子学流弊。在刘宗周看来,东林学者固守朱子学立场却至于思维僵化不知变通,有惨刻不情之弊;阳明学者玄虚放肆之弊引发顽钝无耻、世道沦丧。这种批评正反映出刘宗周的学术担当:基于心学立场,寻求全面克服朱子学和阳明学流弊的思路,以解决时代危机。而晚年刘宗周对白沙自然思想的评价转变,正表明他在接续明代心学学统的基础上开创出全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此即见于下文所述的第二方面。
第二,关于刘宗周自然思想的义理结构。晚年刘宗周转变立场,改为高度评价白沙自然思想,主要原因是他找到了将聂豹与王畿的立场融合为一,以解决朱子学与阳明学流弊的思想道路。他一方面借助白沙的思路,在心体结构中安立一个超越于作为“心之所发”之知觉的形上实体(心之所存);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阳明-王畿一系心学未发已发一体化的思路。前者,刘宗周称之为“静中养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独即天”;后者,刘宗周称之为作为独体之妙的“存发总是一机,故中和浑是一性”。[54]刘宗周使用“意”取代了良知,意与良知同为即存有即活动的性体、心体。不同于阳明将本心的觉识活动视作良知当体自身,刘宗周认为“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也就是说,“意”不是心的觉识活动之现象;而是心之所以为心,是觉识活动得以可能的根据。 [55]由此,刘宗周将本心区分为“所存(未发之中)”和“所发(已发之和)”两个层次。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则是指存先于发、中先于和;中和及存发浑然一体但有分,具有由中导和、由存导发的机制。刘宗周使用“好恶”和“善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来表述该机制:
意根最微,...... 而端倪在好恶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恶必恶,彼此两关,乃呈至善。故谓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着人力丝毫。 [56]
东北某种业公司未经其授权或许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丹玉405号”玉米品种亲本,在生产种子后以其他品种名称进行包装销售。最终被判赔300万元。
意是超越的性体,其超越性首先表现为好善恶恶;因此“好恶”是“性光呈露”,也就是聂豹所说的“实体呈露”,具有善必好、恶必恶的特点。刘宗周将其视为白沙所说的端倪,它是杜绝人为干扰的天道自然之动,具有“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般渊然定向于善的内涵。此所谓自然,具有《孟子·离娄下》“可坐而致”般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意之超越性的另一个表现,则是“意有好恶而无善恶”“意之于心,只是虚体中一点精神,仍只是一个心,本非滞于有也,安得而云无?” [57]善恶是在所发的层面对具体事务之判定;好恶则具有不滞于有无的整全性和普遍性意义,澄然在中。虚体中一点精神,其意义是指好恶不是超越于心的形上实体,而是心的内容,具有生生变化的活泼性。这有点类似于白沙以静虚破除朱子学太严之理,能够避免朱子学天理观限制心之活力的流弊。这种活泼的道德理性观,在刘宗周以元气论述未发已发关系时有更为清晰的说明。
刘宗周认为“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意是贯通天人的生意、自然生机。他把自然生意分为性宗和心宗两部分,分别对应于天道自然与人道自然。 天道自然是离心而言的性情之德,一气流行自有其秩序,分别命名为喜怒哀乐,对应于天道之元亨利贞;人道自然是即心而言的性情之德,心体生化的秩序,也是喜怒哀乐,对应于人道之仁义智礼四德。 [58]由上可知,刘宗周思想中的气和喜怒哀乐,首先是在天道运行的意义上说,而非在下坠为自然主义的实然意义上说。 基于喜怒哀乐而界定的未发已发关系,就表现为:“自其所存者而言,一理浑然,虽无喜怒哀乐之相,而未始沦于无,是以谓之中;自其所发者言,泛应曲当,虽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未始着于有,是以谓之和。”[59]作为气序的喜怒哀乐,是心体,也是性体。就心体而言,未发已发的关系是元气存诸中与发于外的表里关系,不是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元气运行自有其一气周流不可乱的秩序,在元气论的论域中界定心体,能够摆脱在人心觉识活动层面界定良知带来的虚无放肆流弊。就性体而言,喜怒哀乐本身是元气运行之秩序,是活泼泼、不滞于有无的天理。在元气论的论域中界定性体,能摆脱朱子学定理论的僵化之弊。
第三、关于黄宗羲对师学的独特阐释。黄宗羲对其师自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明代哲学自然之辨中具有独特的意义。[60]这主要表现在其对“意”的诠释,以及对“主宰与流行”之辨的诠释:
觉有主,是曰意。离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独矣。故愈收敛,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处停顿,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61]
上引文是黄宗羲对其师思想的概括和评论,清晰展示了刘宗周自然思想的理论效应。主宰与流行之辨源自刘宗周,刘氏提出“主宰处着不得注脚,只得就流行处讨消息”[62]之说,流行是一气流行(已发),主宰则是气之秩序(未发之中)。 这是对刘宗周自然思想的概括。黄宗羲将其师“意”论评价为愈收敛、愈推致,可谓独具慧眼,指示出刘宗周哲学承前启后的开新一面。在黄宗羲看来,刘宗周说的诚意就是阳明之致良知。 [63]这主要是说明诚意学说发挥作用的意义机制,与良知学之事上磨练一样。由于主宰即在流行之中,超越的意根展现为每一事物皆得其理,个别性事物亦由此而呈现其高明广大的意义。黄宗羲将其概括为最收敛之物也是最广大之物,极富深意。事实上,这是对刘宗周总名思想的提炼和说明。刘宗周称:
天者,万物之总名,非与物为君也。道者,万器之总名,非与器为体也。性者,万形之总名,非与形为偶也。[64]
刘宗周此处直接援引郭象《庄子》注提出的“天者,万物之总名”命题,[65]意在强调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然、自生自长,不应将天、道、性视作脱离天地万物别立一层的概念。参照前文所引刘宗周“存发一机、中和一性”的提法,这些命题清晰表明刘宗周心学的特质:一、关注每一具体、活生生的真实,拒斥脱离当下别立一层的虚构物。二、强调万物都是自生、自得、自化、自足的,天(道、性)具体化为万物自生自长内在的通达条理,其意义在于确保每一事物成为它自己。这两点特质也说明了,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与白沙学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强调天地万物均自然伸展而又富有生机地关联为一个整体,这是令天地万物以最高效的方式组织起来发挥创造性效用的天道机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诚意学说以朝向心之意根最微处(内向)用力的方式,却开展出最能通达万物秩序(外向),确保天地万物之个体性与公共性之恰当平衡的内涵。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愈收敛、愈推致。结合钱穆先生的一个评论:“宋明儒的心学,愈走愈向里,愈逼愈渺茫,结果不得不转身向外来重找新天地”,[66]可知其中实际上隐然预示了明清之际学术的新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意的超越性,每一个体事物在实现其自身秩序的同时亦臻于高明广大之境地,展现出心学世界的丰富性与创造性:一方面,更多的个体呈现自身条理,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此之谓道体之无尽;另一方面,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共同体由此奠立。这一思想蕴涵,在黄宗羲的名著《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中有精彩的呈现。学界对此亦有研究,本文不再赘述。[67]
综上,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心与物的政教秩序面向。 晚年刘宗周的自然思想,在保留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存有论义蕴的同时,重点突出政教秩序的含义。其“存发一机、中和一性”的义理结构,既注重由存导发、由中导和,亦保证存与发、中与和的一体性;其理论效应是令超越的意根内在于流动、活泼的现实事物,由此磨练对现实的快速应对能力。这种活泼的理性观,展现了刘宗周、黄宗羲师徒两人浓郁的救世情怀,这是晚明清初心学思想家在面对国家和社会政治危机时刻淬炼出来的解决方案。
四、结论
明代自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潮兴起以来,心成为哲学界首出的概念。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历来众多,本文没有直接研究心的概念,而是通过对于明代哲学家群体围绕自然开展的丰富辨析,探讨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自然”一词在明代心学中并非主要的概念,而是作为解释主要概念的辅助词。然而,这种辅助词有着独特的作用。陈白沙思想以自然为宗,明代朱子学者对其有详尽的批评;而阳明学派聂豹与王畿、甚至刘宗周中年与晚年两个阶段,对陈白沙“自然”思想则有不同的认知与评价,从而分别展开复杂的思想辨析。由此,明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围绕白沙展开的理论辨析,构造出自然之辨的独特思想论域。
本文的论述表明,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重心分别指涉“心”所蕴涵的天道、存有和政教秩序,而非仅仅对自然词义的辨析。具体说来,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辨在时间上是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以上便是本文通过明代自然之辨获得的新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这对于吾人深入理解明代心学的多层次义蕴,显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略作两点分析总结如下:
1. 明代心学的特质表现在开发心的蕴涵和活力,令天道创造性具体而真实地呈现于人的生活世界。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也能够帮助澄清一些误解。例如,明代心学发展出气论的向度,研究者容易有自然主义的印象。然而,通过自然之辨的分析,可知刘宗周、黄宗羲气论思想是在天道运行的意义上说,具有超越性、理想性的内涵。由此,吾人必须正视这种心学之气论所带来的思想新动向。这对于深入理解明清之际新的学风及思想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2. 与西方哲学意义上剥夺了人的社会属性、文明属性的自然状态不同杠杆炒股的app合法吗,中国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是贯通天道、人性与社会政治等内涵的。如前文所引述,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特质表现在守护人之自然本性的基础上确立政教秩序。具体到宋明理学,其关注的核心不只是论述天道自然的秩序,更是涉及以此秩序为基础建构理想世界的途径。由此,理学形上学实际上是理学家对宋明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解决平民化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解决方案的理论探讨。朱子学天理观“所当然”与“所以然”之辨,蕴涵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平衡结构; 明代心学与朱子学之间的理论争端,本质上是对此平衡结构的意义重建。而明代哲学的自然之辨对此展开逐层深入的理论辨析,正反映了明代心学与政教之间复杂的意义关联。


